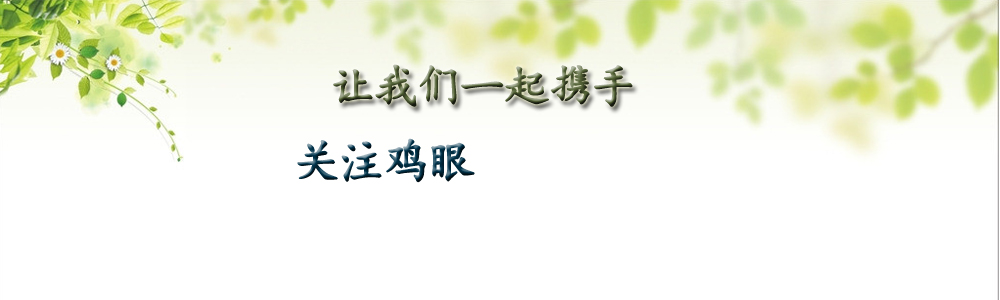母亲短暂的一生2计划
二十多岁女卫生员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给母亲吃了颗定心丸。但是也让母亲潜意识里对这件事掉以轻心,给自己的身体埋下了后患。
晚上,母亲把不能上环的原因说给父亲,也把女卫生员的话说了。
母亲说,我在那儿半天,人家别庄去的人也都上了,就我一个儿没上。你说也不疼不痒哩,瘤子咋长那里头去唻?
平时少言的父亲说,那谁知道你唻,咋长恁蹊跷。
母亲说,就是哩,要是长外头哪儿,咱诊所医生用小刀儿就割掉了,医院花框外钱。
那时,本庄外村,头上脖子上身上长包的人,也常见,小的跟黄豆大,大的跟一个鸡蛋大。诊所医生说是粉瘤,肉瘤,不碍事。只要不疼不痒,在那个最基本吃穿温饱都吃紧的年代,没有哪个人,医院、县医院当病看。
像手上脚上长的鸡眼瘊子,都是大队合作医疗诊所的村医,一刀解决问题,虽然,被割的病号,疼得呲牙咧嘴。
母亲生活的环境就那么一个小村庄。所有见识和信息,都来自于庄上人口口相传。自然得不到很科学很前沿的医学知识。
她只知道,肉瘤不危险,不是十万火急的事。既然专业的卫生员都说了,也不用那么急着去割。
她没听说过,庄上乃至于整个大队里,哪个妇女子宫里长了瘤子,更没听说过,瘤子会要命。
父亲说,明个儿弄到钱了,医院割了。
母亲知道父亲嘴里的“明个儿”只是个计划,不是真的“明个儿”。
正是青黄不接时,缸底的稻子和小麦加一起,一家七口人的口粮,也接不上新麦了。
吃的就不够,还要四处去借抹,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麦子拿集上换钱。
父亲兜里常年没有揣过上五十块钱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分钱没有的时候占大多数。即使年底卖个小猪一百多块钱,兜都暖不热,就要给生产队打“进粮款”,或者还别人钱。
春上头儿借粮难,借钱更是难上加难。
医院割,说少的,起码也要个百儿八十块钱。一时半会儿,算是没指望了。
母亲说,停停再看。
停停看,是我们那里的土话,就是再观望拖延一段时间的意思。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让父亲写毛笔字,打算盘,写个发言稿,那是小菜一碟一蹴而就。可是要让他“混钱”,半辈子,他都没有学会,所以日子一直过得捉襟见肘。
对今个儿没能上成节育环,父亲母亲坐那闲聊一会儿,发愁感叹了一会儿,父亲估计心里琢磨一圈,也没借钱处,就又对母亲说:等麦季下来分了麦,咱就去。
母亲没言语。家里的情况她十分清楚,两个人的工分,要养活七个人,就是麦收了能分的小麦,也没有富余。
再说,有女卫生员(村里唯一女医生,负责接生和看妇科病)的那句话打底,母亲和父亲心里都不认为,这是一件火燎眉毛的十万火急的事,是件应该抓紧时间对待和处理的事。
那时候,经济的拮据医学知识的匮乏,农村人都是“轻伤不下火线”,不躺倒床上不能动弹了,医院,更何况,母亲自己的“不疼不痒”,不影响下地干活挣工分。
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过去,眼看着麦子黄梢了,麦子割了,颗粒归仓了,开始分麦子了。
这是全庄大人小孩儿都为之兴奋的时刻,半年的劳动,终于要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背回自己家里了,可以尽情不省俭的吃上几天白面馍了。
可是因为体质弱的父亲,一个劳动日只能占八分,相当于头等女劳力的工分。
而男劳力头等分十二分,二等分十分。
头等男劳力,干一天就要比父亲多分三分之一的粮食。
虽然母亲能干,干起活来不惜力,可是因为最小的妹妹才一岁多,且体弱多病,母亲经常要请半天假,抱她去大队诊所看病打针。这样,她的工分就只能被评为二等妇女工分,六分。
父母干一天活加起来,刚刚接近人家一个头等男劳力的工分。
可想而知,分粮食时,父母要吃多大亏。
人家兴头头的,用架子车从麦场往家拉小麦,一趟又一趟。
父母亲拉一架子车两架子车,就没有了。
本来将将够(刚刚够)七个人的口粮,可是我们兄妹几个下半年的学费,平时一家大小欠的看病费用,礼尚往来赊欠别人的钱,烟瘾酒瘾都很大的父亲,赊欠烟酒店的钱……都指望卖麦子去还。
父亲的账本上,口粮卖掉一半,也还不上大大小小的拉子(方言:欠款),哪还挤出母亲医院割瘤子的钱?
父母亲又把希望的线延长,商量后说,卖麦的钱划拉不开,咱秋里再去算了。
父母亲的意思,秋天稻子下来,分的粮食会比麦子多。
这期间,母亲自己并没有感觉有啥异常,肚子也不疼不痒。这一点,也是她不当回事的主要原因。
又转眼,到了秋天。
黄澄澄的稻子收割了,分到各家各户了。
我家分得稻子的确比麦子多,因为生产队种的水稻比小麦多。
父母就计划着,等生产队收罢红薯棉花花生等晚秋作物,种完冬小麦,就去卖稻子,医院。
父母刚筹划好,大队又开社员大会了。
会议精神,传达上级计划生育政策,又升级了:五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必须做结扎手术,三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必须上节育环。
费用由公社负责。也就是说,住院全免费。
医院来的女医生,在大会上做了解释,大概说明,结扎手术就是腹部开刀,把输卵管扎起来。
输卵管是干啥的,扎输卵管能不能管住不再怀孕,别说只读过小学二年级的母亲,即使上过私塾自以为有文化的父亲,也是一无所知,毕竟,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不是每个普通人都了解那些专业的医学知识。
但是有一点,母亲听明白了,那就是结扎要开刀,要从小肚子上开刀。
既然必须结扎,必须开刀,何必要开两刀哩?
结扎时给医生说一声,顺便把那个小瘤子一起割了,不是省得受两回罪吗?还省钱了。
母亲回家把她的想法跟父亲提。父亲也觉得,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不过毕竟父亲比母亲见多识广一些,他说,到时跟医生说,看他们同意一起割啵?
母亲高兴得很,觉得这是不在话下的小事儿,想当然的说:那在他们手里,值当个啥,就多割一刀的事儿,又不费劲儿。
(未完待续)
转载请注明:http://www.gmzwc.com/jyzd/15042.html
- 上一篇文章: 江苏3大奇葩小吃让人胆怯,苏大强们喝3款
- 下一篇文章: 民间俗称鸡眼草,老中医均认识它,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