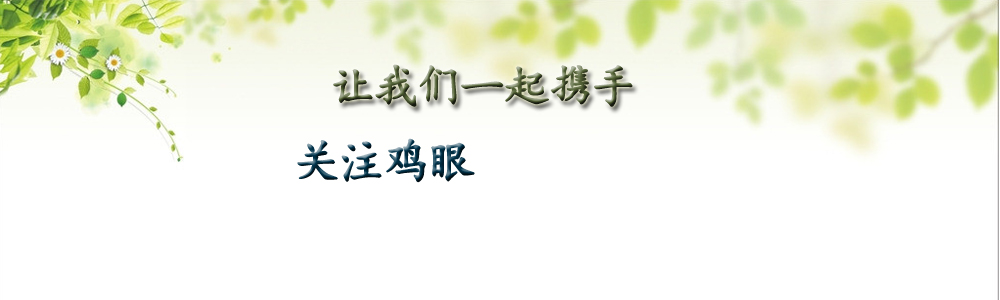乡音天台话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天台话之难懂,可能名列台州各县(市、区)方言之首(当然玉环坎门一带的闽南话同样难懂),我花了两年时间终于听懂了天台官话,但是到天台乡下去了一趟,七十多岁的老人方言俚语一说,我又傻眼了。据说,二十多年前的自卫反击战,越南兵破译了我方的密电码,我军指战员遂叫两个天台兵临时充当报话员,听得越南人直翻白眼。
临海人讲话糯搭搭,天台人讲话硬呛呛,一开口,好像平地一声雷,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天台人以大嗓门居多,男女老少,高门亮嗓,声若洪钟,讲话像打雷,调情像吵架。两个天台人在上海的大酒店吃饭,饭罢在酒楼里抢着买单,双目怒睁,有睥睨一切的气概,边上的上海人看了吓得要死,以为他们要打起来了。所以,宁听临海人吵架,勿听天台人说话是有道理的。天台有一句俗语说“腰中三分铜,讲话如雷公”。其实,天台人就是一文不名,讲话声音也是大过雷公的。
天台话说出口,有“大石小石落铁盘”的感觉,硬得让人感觉天台话会往下坠,配合他们的硬气倒是相得益彰,我很难想像一个天台大男人操着吴侬软语的绵软样。不知是天台话的硬度导致了天台人的硬气,还是天台人的硬气造就了天台话的硬。
天台话硬而重,而普通话字正腔圆,天台人普通话说得好的不多,让四十岁以上的天台人说普通话,十有八九让人笑掉大牙。
天台的文化底蕴太深厚了,从天台话里就听得出,中午叫“日昼”,晒太阳叫“摘日头”,厅堂叫“堂前”,你叫“尔”,看戏叫“相戏”(看电影则叫“望电影”),立即叫“旋即”;学费叫“束修”,“束修”一词出自《论语》,一个七旬老娈人问自己的孙子学费交了没,开口便来一句:“你束修交了没有?”就是教古汉语的博士生导师也未必能把这个词用得这么自如。
在称呼上,天台人也是独特的,夫妻在人前称呼自己的另一半,就在子女名字上加上“那”字,如土根那爸,土根那姆,“那爸”、“那姆”难道还有“这爸”、“这姆”不成?他们管姐叫“大”,管妻舅叫“冷饭舅”,让人弄不明白。天台人称呼之间显得格外热络,长辈必以“公”、“叔”称之,同辈人之间相互都以“哥”、“妹”互称,有个杭州姑娘找了个天台人当男友,初次跟男友回天台,走在乡间小道上,时不时有妙龄村姑跟她的男友打招呼,开口闭口“某某哥”,言谈之间甚是亲昵,听得杭州姑娘醋意顿生。
在天台话里,没有“爱”字,只有“中意”一词,有人替天台人担心,那天台小伙求婚时效果会不会打了折扣,不必担心,天台人求婚时有更浓烈的表达方法——“你死后愿意葬在我家的祖坟里吗?”意谓生死与共,还有比这更强烈的爱情吗?
还有,天台话里的“脚刺”指本领,我常犯嘀咕,“脚刺”算本领,那“鸡眼”又指什么?天台人管马铃薯叫红毛芋,红毛者,洋人也。
天台话里的感叹词特别有意思,如“啊呐!碗敲碎了。”“啊呐呐!咯讨债鬼竟会作咯档事”,表示惋惜;用“咋好”表示无可奈何,“一勿会种田地,二勿会做生意,咯档人咋好!”,用“弗火落”表示无可奈何,“天台人三厨薄,一天没粥弗火落”。
天台人很热爱自己的语言,不容别人置啄,在天台街头,一个自以为是的上海人学着天台人说话,结果天台汉子把他扇了一顿,旁观的天台人齐声喝彩,说:“打得好!”警察也睁只眼闭只眼,说:“活该!下次还学不?”弄得这个上海人灰头土脸的。
天台人是特立独行的,天台话自然很难被别的什么方言浸染,如果这世界上还有最后一种方言没有消失,恐怕就是天台话,几乎所有的天台人都以操一口天台话为荣,外县市人到市级机关工作后,多多少少改变口音,被当地方言所同化,但天台人自始至终不改,极少有天台人改说别处的方言,你说天台人死心眼也罢,说他们热爱家乡也罢,反正就是这样,这一点上跟仙居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善于审时度势的仙居人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实在不行,中庸点,改说普通话。
而天台人是死硬派,走到哪里,硬梆梆的天台话就操到哪里,如果一个天台人不说天台话而说别的什么话,其余的天台人把他归入异己,心里鄙薄道:“不配做天台人。”天台人一听到对方说乡音,多半会引为知己,就像列宁说的《国际歌》,只要哼着它的曲子,就能找到自己的战友,天台人也一样,想找老乡办事,天台话就是最好的通行证,不管在哪里,只要听到天台话,天台人心里就踏实。
作者简介王寒,报人、作家。浙江台州人,出生于杭州,天台媳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好读书,好码字,好旅游,好音乐,好园艺,好美食。出版著作《花事》、《少见多怪王小姐》、《刀子嘴豆腐心》、《纯属戏说》、《城市的良知》、《行走新疆》六部。近年来致力于台州文化的研究和解读,著有“台州人文”系列四部:《台州那些风雅事》、《倾听台州大地的耳语》、《味蕾上的台州》、《大话台州人》;最新作品《无鲜勿落饭》。本文原题为《最硬不过天台话》。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gmzwc.com/jyzl/8410.html
- 上一篇文章: 你不需要知道的摄影装B名词释义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