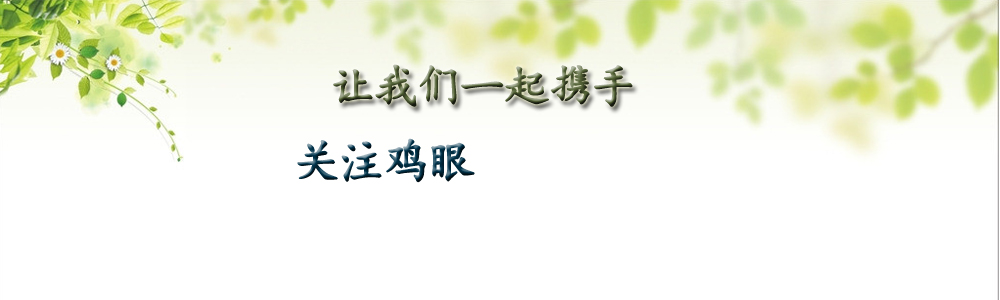垣曲古城漫话上
说垣曲,撇不开古城。古城作为垣曲的老县城,作为垣曲的富庶之地,作为垣曲最大的村镇,少了它,就像缺了盐、少了醋,乡土的这道菜肴也就没滋没味了。
古城,这个听起来很古老的名字,其实在垣曲地名序列中,只有五十来岁。古城原来叫城关。在中国北方,大凡叫“城关”的都是县治所在地。年县城搬到了30公里外的刘张,取名新城。县城搬走了,再叫城关就有点不合时宜了,于是年改称“古城”了。
其他地方也有叫“古城”的,但往往在前面加上说明,如“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直呼古城的恐怕不多,唯独这个地方才能担当起古城的称谓。史料载:“本地初名阎家阁,西魏大统十六年(年)县治迁此,宋称大赵村,明设进贤、安民二里,清康熙三年改进贤坊、安民坊,民国三十四年()二坊合并为城关镇,民国三十七年()改称城关村。县名屡变,频易历属,而渐直至年末迁……”当时为古城拟名的人一定深谙古城历史,取其古城之名,绝对实至名归。
作为县治,当然是城,是垣曲的大城市。至于面积大小、人口数量,没有标准,也没人去追究。就连历史上曾经的“大赵村”“安民坊”“进贤坊”这些村名,也被城关掩饰了,无关紧要了。当然也有了“垣曲城”“城里”“城价”这些俗称。以至到后来,新城越建越大,古城越叫越响,就很少有人知道城关这个名字了。小浪底水库修建,古城彻底留在了库底,若干年后再发掘,当还是名副其实的“古城”。只是古城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仍叫古城,也有叫“新古城”的。
就让我们从记忆中追寻古城,搜索古城,在纸上勾勒出昔日古城的轮廓吧。
厚土从西原岭头呈扇形绵延下来,成了一个台塬,古城就在这个台塬上。沇河在东边直直冲下来,到这里叫东河;亳清河从西边流下来,从城南绕过,到这里成了南河。两条河在东南边不远的地方汇在一起流进了黄河,就有了清河口。两条河托起一座城,西北倾,东南出,势如卧牛。
东边是东河槽,河槽东边一条岭绵延到黄河边,叫“凤凰山”。山脚下全是石头,叫“墩底下”。有泉水涌出,生螃蟹。西边是西河槽,河水在城西迂回了个湾,也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西河湾”。城北高,城南低,城就挂在台塬上了。过了南河,鸡笼山伸下来又是一个台塬,东西走向,叫“寨坪”,遮住半个城,也就有了“南坡”。台塬东端有人家,叫“南观”。黄河就在不远处,看得见波涛汹涌,听得见吼声响雷,闻得到土味鱼腥。黄河南岸横亘着一溜儿的山,到东南方突兀高耸,叫“黛眉山”,属河南省新安县地界了。山在河南,景现河北,山势雄伟,层出叠翠,天然屏障,庇佑河北。山脚下黄河缠绕,有帆影点点、渔歌唱晚。更令人称奇的是山脚下有座小山,形如雄狮,面南而卧,人称“狮子山”。狮头、狮身、狮尾清晰可辨。尤其是那几块梯田,恰如其分巧夺天工地成了狮子脖颈上的皱褶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为河北的这座城平添了几分风水。
城依水驻,水绕城流。有山就有了厚重,有水就有了灵性。是山城,亦水乡,既有黄土高原粗犷,又有江南水乡韵味。假物喻灵,就有了关于这座城的美丽传说。相传,大禹治水来到这里。彼时,这里是一巨大湖泊。大禹行至,不禁惊叹:“金津玉液,水退必为宝地。”遂寻思:此乃帝舜故里,不可大斧导浚,须假以灵物。于是,令随从牵来一头硕大黄牛,体型如丘,背脊似岗,拴于湖北三里之处,将一颗玥珠嵌于牛额,谓牛曰:“你要永卧此地,饥食白云,渴饮湖水。”然后又牵来两条龙,令其一由北向南游,到湖口绕牛之东;另一条由西北从横岭关向东南游,绕牛之南。直至湖水退干,化为沃土,然后游入黄河。又招来一对凤凰,一立于湖之东,一栖于湖之西北,和鸣催战。黄牛忠于职守,化为隆起的岗地,后人就在牛背上建城,因而叫“卧牛城”;二龙依令行事,昼夜不怠,终使湖水尽退,自己化为现在的沇河、亳清河。两水相绕,恰似“二龙戏珠”。至于凤凰,化成城东的“凤凰山”,城西北的“凤凰台”,护城兆祥。因此,又名“五灵城”。
传说毕竟是传说,不足为凭,文物考古为证。此地处中华腹地,依偎黄河母亲,有山有水,最适于人类繁衍生息;上有三门峡,下有八里胡同,是黄河从黄土高原流向中原大地的最后一座城郭。上世纪初,中外科学家就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从年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在寨坪的土桥沟找到中国第一块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百余年来,在古城及其周边的考古发掘一直就没停歇过。商城遗址、东关遗址、宋代遗迹相继发现;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在这里都有。一座灰坑发掘出一种文化,一堆瓦砾拼起一个朝代。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瓷器、铜器。古城的历史都在这坛坛罐罐里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寨坪土桥沟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具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曙猿化石,更是惊俗骇世,令天下哗然,把人类出现的历史向前推进了l万年,证实了人类远祖起源于此。在今天的新古城街头,赫然矗立起巨石,写着“人类从这里走来”。天下谁敢出此言?唯独山西垣曲古城。
志书中是这样记述的:“……北靠历山,南濒黄河,东辅王屋,西弼中条。封门口扼其左,横岭关制其右。沇河、亳清河分东西合抱,气候湿和,土地肥沃,既为晋豫孔道,又为富庶之地,便交通,利农耕……”确为钟灵毓秀之地,“葛伯春耕”“阳壶返照”“洪庆晓钟”“黛嵋晴岚”,垣曲古八景这里就有一半。清河口逮鱼,墩底下摸蟹,南河捉鳖,沙燕窝掏鸟,南坡上逮蝎,东河滩养鱼,南门口种菜,黄河滩上务果园、刨花生……30岁以上的古城人,谁无此等记忆。
城在台塬上,北高南低,呈坡状,像是挂在天地间的一幅画。是城当然有城墙,城墙依地势绕城构筑,像是给城镶了个框。条石筑基,夯土筑墙,青砖包面,高大浑厚,墙头可以行人走马。不知道当年有没有城垛,有没有角楼。岁月和历史只留下了残垣断壁。
城门有三座。北门叫“富春门”,南门叫“万安门”,西门是“永丰门”。没有东门。相传开了东门,要出“一石二斗芝麻官”。既然能出官,为啥不开?其实东门外就是东河槽,东河水急,难免惹是生非。没开东门,出不了一石二斗的芝麻官,倒是住了不少人家,叫“东关”。
西门也没有了,残缺的城墙,不深的壕沟,分出城内城外。一大片的人家,叫“西关”。据说当年的阎家沟和大赵村就是这里。
城南是河滩。是全城最低的地方,城里的水都往这里流,也有城墙,墙根有流水的涵洞,叫“水门”。城墙外就是南河,发了水,河里的水要进去,城里的水要出来,厚实的城墙也奈何不得。县志里记载的“城南频遭水灾,城墙屡圮”就是这里。县城的搬迁,就是这地方惹的祸。南门也早已没有了踪影。有门就有关,出了南门就是河滩,“关”不能在河滩里,有失体面。但关还得有,过了河是寨坪的东端,坪头有人家,属城里管,就算是南关。此处地势高,能看得见黄河,过去有观河亭,有刻着“天上来”的石碑,叫“南观”。垣曲话“关”和“观”的发音很独特,上扬下平的语气一听就知道是“关”还是“观”。外地人辨声听音,又有谁去咬文嚼字地问是“南关”还是“南观”呢?
北门还在,只是成了土台子。门洞被垒往了,当年县太爷骑马坐轿的风风光光、百姓商贾进进出出的煕熙攘攘,都被垒进了门洞。城门上“富春门”的匾额经岁月剥蚀的依稀可辨。门楼顶上有稀稀疏疏的茅草,几株永远长不高的椿树、构树,向人们诉说昔日的春秋,曾经的繁荣。
城墙、城门,就像住户宅院的院墙和大门。在中国历史上,城墙、城门,是城的标志、权力的象征、繁荣的体现。有了城墙、城门就有了关,成了城关。一个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被围在这高大厚重的城墙中了。我们无法去追溯历朝历代县衙官府的行政机构,那是文物考古的事了。人们的记忆存储在近代史上。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古城一直是县治所在。世事更迭,时局动荡,国民政府,伪顽政权,日本侵略,都以城为目标,进了城就是有了名分,占了城就是占了县。垣曲的大事要事都发生在城关,城关发生的事就是垣曲的事。据说,流传至今的垣曲“催眠曲”:“昂、昂、逗价价”中的“麻胡”就是从城里蹿到东滩的。可见,当年的城关在县里人心中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五灵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人民政权在这不大的城里设署办公。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排民房就是县委、政府,公、检、法在三间瓦屋里办公。“仓堎上”是文教系统,“水门底下”是农业单位。县委书记、县长借宿百姓家,四合院里住着农户,也住着县里的干部。当然,作为新的政权,也要建设,盖几间瓦房就成了好单位,房子建得大,盖得高就成了大礼堂。以至于若千年后,城里人还把当年的机关单位作为地标,如数家珍地说当年政府就在这里,那儿是公安局,那儿是文化馆。当然也有人津津乐道地说:县长就住在我院的东厦;组织部长和我是邻居;县委书记的小娃和我一块耍大。
年,县城搬走了,机关单位搬走了。留下了城关,留下了城,也给城关人留下诸多遗憾——县城要在咱城关,一定建好了;县城要不走,咱就是城里人;县城要不搬,咱也不用坐车跑六七十里去县城;今天也不用往县城里挤。城还是那座城,只是少了一个“县”字,性质就变了,内容也不一样了。
是城当然有市。对县里人来说,最具诱惑、最让人羡慕的当属城里的街市了。据说原先的街道是在后来的石坡上,你咋也想象不出曾经作为老城街道的存在。拐拐弯弯的曲径通幽,七尺竹竿横着都拿不过去。路面倒是用卵石铺成的,不扬尘,不沾泥,只是走在上面咯脚,幸好当年没有流行高跟鞋。至于商铺,没有留下丁点的迹象,到后来两边的院落大门连檐接拱钩心斗角地成了胡同。
后来的街道不知是啥年代开的。北城门西边的城墙挖开了一个豁口,一边各垒了一个高高的砖柱,顶上有一个石灰捏成的圆球,用红颜色抹了色,没几年就“灰不拉几”了。倒是用铁条打的拱形半圆,顶在两根柱顶上面,锈锈斑斑地存在了好多年。街道通到了南门口。街不长不宽,坡依然存在,走不远就下坡,两边的房屋顺坡构筑,呈阶梯形,一溜的南高北低。走在街上,朝南看,只见得一颗颗的脑袋,向北看,是一条条的长腿。往南走,得抬头挺胸;朝北走,要俯首弯腰。山里的城,要符合山里的特点,上山下坡地惯了,平了,大概就走不成路了。街不长,不用极目,就瞅到了街头。北门口一声吆喝,南门口都能听到,一家炒辣椒,满街打喷嚏;一家饭铺熬羊汤,满街都是膻腥味。
南北一条街,东西也有一条街,号称“十字街”。只是“十字”的这一横写得太短,东走百十来步就到了城壕沟,往西四五十步就进了戏台院。
过了十字街,是条丁字街,只有西边一截,历来是行政中心,原先县委、县政府机关单位都在这一片,后来镇政府、招待所、法庭、税务所、党校、农机公司都在这条街上。东济公路从西关进来,穿城而过,既是街又是路。到街口,司机刹车踩不精准,方向盘扭不到位,还要打倒车才能拐过来。街口的房角常被剐蹭,汽车开进门市部的事时有发生。
因为曾经是县城,因为历史太悠久了,因为县城搬走了,因为要修小浪底水库,大概也因为这地方迟早要淹没,几十年间,街道格局不变,建筑不变,瓦房与楼房并存,土墙与砖墙都有。就是门脸,有一块块木板拼装的栅板门,有安了合页的新式门,也有时髦的玻璃门。走在街上,恍惚从民国到现代一路走来。如果没有搬迁,稍作美工,一定是不错的影视拍摄基地。
就是这么长,就是这么宽,就是这么几道街。商品不以街道的长短而缺失,买卖不因门市的大小而兴衰。供销社、信用社,粮站、棉花站,农机站、食品站,药材公司、新华书店,照相馆、镶牙馆,理发馆、裁缝铺,油坊、弹花柜、铁匠炉,饭铺、旅店,药铺,卫生院、兽医站,在这不大的街道上都有一席之地。吃的、住的、穿的、用的,都有卖的,都能买到。大街上,卖菜的过来撂下担子就有了交易,搁张桌子就有人拔牙,放把小凳就开始割鸡眼……
长了,吊涎;短了,局促。宽了,空荡;窄了,拥挤。三五个人走在街上不显得寒碜,十个八个人在街上就有了热闹。只是每年四月初八,腊月初八的两次会,就有些拥挤不堪了。四面的货来了,八方的人来了。买卖多,人多。到处摆摊,满街是人。北来的从北门口挤到南门口,南来的从南门口挤到北门口,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到处是人挤人。摆摊人叉开两条腿,展开两只胳膊护着摊子,哪能顾得卖货。拿杈把扫帚的得朝天竖,钉把镰买把锨也要举起来,一不小心就蹭剐了别人的衣服,伤了皮肉。买顶草帽戴在头上,抬手一摸没有了,回过头看看,别人头上也是戴着草帽,岂敢槽头认马、头顶夺冠。有往前走的,一个劲地喊“油”“油”“油”,起初兴许还有人躲闪,吆喝多了也不灵了。赶一天会,出几身汗,踩坏了鞋,挤丟了钱,不说地方小,只说“会”热闹。倒也是,平日里山坡野岭地松散惯了,只有一年城关的这两次会,才能享受到如此的拥挤。何况赶的是城里的会,在城里挨挤,再受症也感到愜意。
从私营到国营,从商号到门市部,多少年来,城里的街道没变,生意也没变。山里的城,山里的人,人们对城关的商业记忆仍然是梅氏镰、张氏镢、老谢照相、老韩镶牙,李家的裁缝铺,赵家的绸缎行,百顺娘的油茶,丁酉的饹唠锅盔……如今说起当年老古城的街市,连说带比划,要不拾根草梗,在地上给你划拉一番,用地图为你演示方位地点,有形有色,甚至都让你觉得有了味道。虽然古城躺在了水底,但淹没不了人们对物产的怀念,乡愁的记忆。(裴聪敏)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gmzwc.com/jyzd/7266.html
- 上一篇文章: 乳房不摸,可能被割教女性朋友学
- 下一篇文章: 最最难找的方子,家家户户都需要,赶紧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