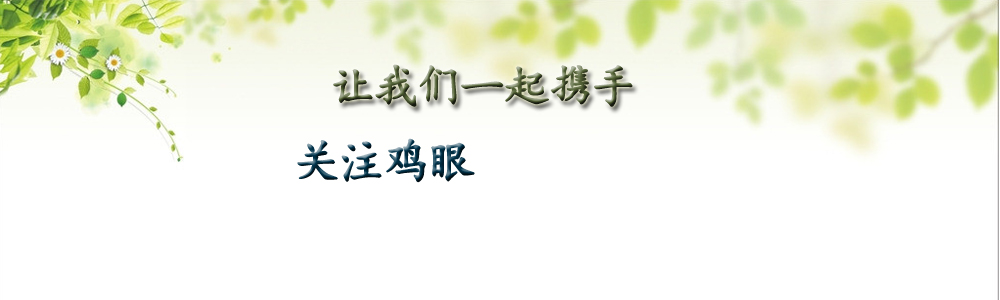王清宏母亲大秦文摘征文NO128
大秦文摘征文作品展︱NO.期
▼
编号《母亲》︱文/王清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暗中时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每每读到这些诗句时,总觉得真是道尽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心理。从九八年开始,我便在外漂泊,求学,工作。母亲更是饱尝了这种心理煎熬,归家时,母亲满心欢喜,洒扫尘除,欢呼雀跃;临行前,母亲潸然泪下,左叮咛右嘱咐,车走好远了,母亲还站在山头眺望。
母亲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与泪水。母亲姊妹六个,在家中排行老二,在她之前有个哥哥。姊妹俩从能干活起,就承担起了家里的所有伙计。老爷在外谋生,外婆在家操持家务,照料孩子。七岁时,外婆生下母亲的二弟,没有灶台高的母亲站在小凳上,给外婆打“定心汤”(生完孩子后慰劳孕妇的汤饭),在缺吃少穿的年代,煮两个荷包蛋就是最优厚的待遇,家中仅有的两只鸡蛋,母亲一只鸡蛋打在锅里,一只鸡蛋打在灶台上,结果被外婆训斥了一番。随着弟弟妹妹的出生,母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看弟弟妹妹,所以求学成为母亲此生最无缘的事情。很多次自己打着火把,送自己的弟弟妹妹到十五里外的学堂去上学,自己只能远远地看着,看着弟弟妹妹踏进学堂的大门,自己还得回家和哥哥到大队公社去挣工分,挣一家的口粮。
在大队挣工分时,母亲和哥哥攒足劲干,休息时,她和哥哥就会在田间地头砍柴,等歇工回家时,姊妹俩都会背一捆柴回家。村里的村民,总会投来艳羡的目光,还啧啧地称道:“不知道这个姑娘以后会便宜谁,里里外外一把好手。”
到了母亲出阁的年龄,经媒人介绍,母亲嫁给了父亲。结婚后,母亲依然勤劳,孝顺公婆,团结妯娌小姑小叔。刚嫁来时,母亲看不惯婆家人的相处之道,父亲脾气暴躁,和兄弟姐妹关系紧张,兄弟姐妹称父亲为“孤老”,父亲不招家人待见。父亲见妹妹衣冠不整,便会拳打脚踢,甚是粗暴。母亲嫁来后,给父亲做工作,批评父亲的暴力行为,在母亲苦口婆心的几番“批判”后,父亲慢慢有了很大的改变。从此,家里便有了和谐的家的气氛。
土地承包到户后,父亲一家就分了家,母亲父亲分到了一口锅,两双筷子,两个碗,三间破烂的房屋,三亩贫瘠的薄田,从此父亲母亲自立门户,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随着三个子女的降临,家中的负担与日俱增,但是母亲依然如故地承担起了家里所有的重活。父亲是村支书,常年不是收缴农业税,走村串户搞计划生育工作,就是搞长防林业建设,经常早出晚归,净忙活着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宜。母亲既要抚育三个孩子,还得忙活地里的活儿。隔三差五的父亲还会将市里、县上、乡镇上的领导带到家里,母亲一见领导到家了,就会开始忙活了,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菜、大肉、白米,母亲总会拿出来,做出一桌好菜,招待那些不曾认识的人。母亲常给我们唠叨:“自己吃了不顶啥,家里不招待个客人有啥劲儿啊?”
母亲未曾进过学堂门,一字不识,所以她总给我们说:“好好念书,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想要出个远门,连个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所以哪儿都不敢去。”所以再苦再累再难,母亲总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不要放弃学业。
父亲脾气暴躁,偶有家庭暴力事件,只是我们都未曾亲眼见过。有一次母亲被父亲暴打,母亲在床躺了好长时间,也不曾看医生。“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父亲打母亲的事件被传到十里八乡,偶有听到别人议论,戳父亲的脊梁骨,母亲娘家人来找父亲的麻烦,母亲连连替父亲说好话解围:“责任在她,与父亲无关。”娘家人也只得作罢,不再追究。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正念初二的我对母亲说:“妈,我不念书了,在家照顾你。”母亲听后,勃然大怒:“你不念书,干什么啊?想学我一样吗?赶紧去学校,上学去!”此后,我就安心读书,直至大学毕业,有时我想如果没有母亲的执意坚持,我也许永远都不会走出秦巴大山,和大山里的乡野村妇没什两样。
不谙世事的我们,和母亲聊起父亲的家庭暴力时,我们总觉得母亲不知道反抗,为啥不知道报警啊。母亲总说:“你爸爸脾气暴躁,我也硬碰硬,这个家就散了,忍忍就过去了。还得为你们姊妹三个考虑,男人脾气暴躁是不会顾忌后果的,恨不得将你打死,以解心头之恨。”母亲偶尔还和我们说起:“如果不是你们三个孩子,我还不如一死了之,不受这人间的苦了,一想起没娘的孩子可怜,就不忍心。有一次被你爸气得我在地头哭了三天,手里拿着毒药,硬是舍不下三个孩子,我将毒药扔进了山中的草丛里。”每每听到母亲说这话时,眼泪总会顺着脸庞悄悄地滑落,随着岁月的更迭,慢慢地也明白了母亲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已经将隐忍和坚强写进了她的生命里。
母亲心底善良,孝敬、善待老人十里八村都是出了名的。奶奶是一个厉害苛刻的农村老太太,母亲刚嫁来时,受尽了奶奶对她的白眼与“调教”,但母亲总会隐忍地接受,不会有多少反抗。不管奶奶怎么做,母亲对待老人的态度总是温顺的,轻声细语,也许母亲不知道“孝”的最高境界就是“顺”,但她用言行已诠释得淋漓尽致。
古语言:”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幼子。”这在我们家表现得最为突出。分家以后,奶奶和小叔一起生活,不管大小的事情,奶奶都会偏袒小叔。九十年代生活条件慢慢好转,吃饱穿暖已不再是难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奶奶依然会给小叔节省,在奶奶的潜意识里,我们家煮的白水挂面都比小叔家的大鱼大肉好吃。所以每次我们家煮挂面,母亲总会给奶奶盛一大碗端去,更别说做大鱼大肉了。受到母亲的影响,母亲一做好吃的,我们便给母亲说:“我们去叫奶奶吃饭了。”母亲也会非常爽快地答应。
后来奶奶年龄大了,不幸瘫痪在床,母亲也会依然如故地尽她所能照顾奶奶,在我的印象里,奶奶被褥的拆洗缝补,端茶倒水,伺候起居,成了母亲常年的家庭作业。奶奶逢人也总会给人说起母亲的孝顺。
后来我求学在外,一回到家就会跑到奶奶的床前,奶奶一见我便说:“你终于回来了,我就等着你回来,我的手指甲、脚趾甲都长好长了,还有鸡眼,难受得很,你赶快给我剪剪。”奶奶是裹脚,总会长鸡眼,时间长了不剪就会很疼,脚臭,所以她很少让别人给她剪指甲,可现在自己身体不能蜷曲了,只能求助于我了,我也会毫无怨言地欣然接受。只是心里总会有一丝黯然的伤感,奶奶当年的威严与霸气已被岁月洗尽。
母亲除了孝敬自己的婆婆,还善待身边的老人。在我家旁边住着一位孤寡老人,母亲让我们叫她“大姑”,因为她和我们同姓。大姑的生活全靠村里人接济,当然做好吃的了,母亲也会把她请到我家来吃饭。每年年终父亲都会到各家去给她收救济粮,一家五斤十斤不等,玉米、小麦、大米(不过那个年代,大米给的很少)均可,村里人也会毫无怨言地上交。条件艰苦时,吃水便是一大难题,八九十年代各家全靠肩挑水吃,天旱时要走好几里路才能挑一担水。我家挑水的任务基本全靠母亲,父亲常在外奔波,我们年龄尚小。母亲每次挑水时总会想着给大姑挑一瓮水,够她吃好几天。受母亲的影响,有时母亲不在家,我们见大姑瓮里没水了,我们也会去给她担水。
印象最深的就是年龄小,挑不动一担水,我们姊妹三个就一起抬,我年长,走中间,弟弟和妹妹一前一后,晃晃悠悠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着,很多时候,一担水等抬回家就只剩两个半桶了。也许在那时并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做,也许善待老人被母亲的言行默默地,深深地诠释进了我们的心里。
如今,我们姊妹三个都已成家,母亲经常给我们说:“要孝敬老人,善待老人,不要对老人呼来唤去,趾高气昂。”挂在她嘴边的话语就是:“轻轻说话不费力,不要给老人脸色看。”也许她不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百善孝为先”的至理名言,但是她的言行让我们学会了宽容与善良,学会了理解与体谅,学会了感恩。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母亲不识字,她给我们的是生命的教育。母亲没有多么深奥的学问,但她用她的言行践行着世间最美的品德,正因如此,也影响着我们做一个勤劳、善良、坚强、感恩的人。感谢母亲一路对我们默默无闻地教诲,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至理哲学,却有一颗如金子般闪亮的心陪伴着我们成长。
王清宏作品编号-END-
▼
About︱关于作者王清宏,陕西紫阳人,中学一级语文老师。
▼
中国.西部文艺微刊
致力于优质的阅读体验
长按北京白癜风研究中心治疗要多少钱北京那个医院治疗白癜风最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gmzwc.com/jyzd/5459.html
- 上一篇文章: 史上最全的东北话大字典,富拉尔基人自
- 下一篇文章: 常见的皮肤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