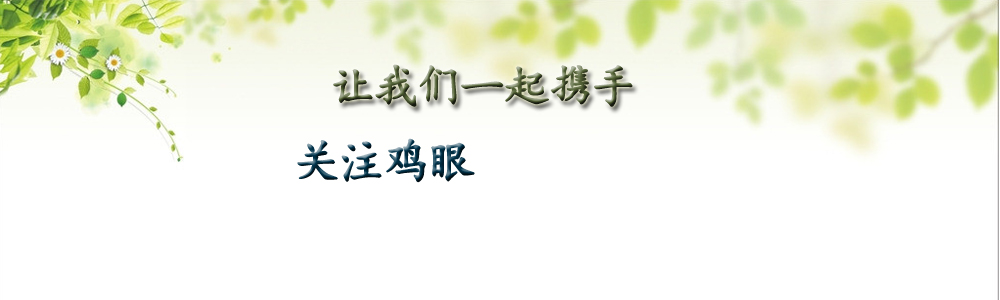裴聪敏丨散文垣曲古城
黄河原创文学
文学公众平台
黄河原创文学
文学公众平台
作者简介
裴聪敏,山西垣曲人,电影工作者。中国电影放映协会会员,垣曲县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垣曲县舜文化研究会理事。曾在《电影故事》《新电影》《电影普及》《舜乡》《舜文化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热衷研究垣曲人文、民俗、农耕文化。
垣曲县政府(古城)早就想写写古城了,迟迟动不了笔,也不敢动笔。一是,古城曾经是县城,是垣曲的大城市,名地方。莫说历朝历代,就是这些年,见诸文字的不少,该写的都写了,该用的词都用了,就差掘地三尺了,就那么一块地方,再写也写不出新意来。二是,十几年前《古城村志》就出版了,书里写尽古城的地形、地貌、历史、人文、掌故,图文并茂,厚厚的一大本,精装。再写,也是在这本书里徘徊。再则,老古城虽然沉在了库底,成了浩瀚的水泊,只有十几年的光景,人们的记忆犹在,历史仍然在碧波中荡漾。写的不像是杜撰,写浅了没意思。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下了题目。写垣曲,不能没有古城。何况,作为垣曲的老县城,作为垣曲的富庶之地,作为垣曲最大的村镇,少了古城,就象缺了盐少了醋,乡土的这道菜肴也就没滋没味了。古城,这个听起来很古老的名字,其实在垣曲地名序列中,只有五十来岁。古城原来叫城关。在中国北方,大凡叫"城关"的都是县治所在地。年县城搬到了六十里外的刘张,取名新城。县城搬走了,再叫城关就有点不合时宜了,于是年改称"古城"了。其它地方也有叫"古城"的,但往往在前面加上说明,如"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直呼古城的恐怕不多,唯独这个地方才能担当起古城的称谓。史料载:"本地初名阎家阁,西魏大统十六年(年)县治迁此,宋称大赵村,明设进贤、安民二里,清康熙三年改进贤坊,安民坊,民国34年()二坊合并为城关镇,民国37年()改称城关村。县名屡变,频易历属,而渐直至年未迁……。"当时为古城拟名的人一定深谙古城历史,取其古城之名,绝对实至名归。规模宏大的古城城墙作为县治,当然是城,是垣曲的大城市。至于面积大小,人口数量,没有标准,也没人去追究。至于历史上曾经的"大赵村",“安民坊”,"进贤坊"这些村名,也被城关掩饰了,无关紧要了。当然也有了"垣曲城"、"城里","城价"这些俗称。以至到后来,新城越建越大,古城越叫越响,就很少有人知道城关这个名字了。小浪底水库修建,古城彻底地留在了库底,若干年后再发掘,成了名符其实的古城。只是古城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仍叫古城,也有叫"新古城"的。就让我们从记忆中追寻古城,搜索古城,在纸上勾勒出昔日古城的沙盘——垣曲古城鸟瞰
厚土从西原岭头呈扇形绵延下来,成了一个台塬,古城就在这个台塬上。沇河在东边直直冲下来,到这里叫东河;亳清河从西边流下来,从城南绕过,到这里成了南河。两条河在东南边不远的地方汇在一起流进了黄河,就有了清河口。两条河托起一座城。西北倾,东南出,势如卧牛。东边是东河槽,河槽东边一条岭绵延到黄河边,叫"凤凰山"。山脚下全是石头,叫"墩底下"。有泉水涌出,生螃蟹。西边是西河槽,河水在城西迂迴了个湾,也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西河湾"。城北高,城南低,城就挂在台塬上了。过了南河,鸡笼山伸下来又是一个台塬,东西走向,叫"寨坪",遮住半个城,也就有了"南坡"。台塬东端有人家,叫"南观"。黄河就在不远处,看得见波涛汹涌,听得见吼声响雷,闻得到土味鱼腥。黄河南岸横亘着一溜的山,到东南方突兀高耸,叫"黛眉山",属河南省新安县地界了。山在河南,景现河北,山势雄伟,层出叠翠,天然屏幛,庇佑河北。山脚下黄河缠绕,帆影点点,渔歌唱晚。更令人称奇的是山脚下有座小山,形如雄狮,面南而卧,人称"狮子山"。狮头、狮身、狮尾,清晰可辨。尤其是那几块梯田,恰如其分,巧夺天工地成了狮子脖颈上的皱折。维妙维肖,栩栩如生,为河北的这座城凭添了几分风水。城依水驻,水倚城流。有山就有了厚重,有水就有了灵性。是山城,亦水乡,即有黄土高原粗犷,又有江南水乡韵味。假物喻灵,就有了关于这座城的美丽传说:相传,大禹治水来到这里,彼时、这里是一巨大湖泊。大禹行至,不禁惊叹:"金津玉液,水退必为宝地"。逐心思:此乃帝舜故里,不可大斧导浚,须假以灵物。于是,令随从牵来一头硕大黄牛,体型如丘,背脊似岗,拴于湖北三里之处,将一颗玥珠嵌于牛额,谓牛曰;"你要永卧此地,饥食白云,渴饮湖水。"然后又牵来两条龙,令其一由北向南游,到湖口绕牛之东;其一条由西北从横岭关向东南游,绕牛之南。直至湖水退干,化为沃土,然后游入黄河。又招来一对凤凰,一立于湖之东,一栖于湖之西北,和鸣催战。黄牛忠于职守,化为隆起的岗地,后人就在牛背上建城,因而叫"卧牛城";二龙依令行事,昼夜不怠,终使湖水尽退。化为现在的沇河,亳清河。两水相绕,恰似"二龙戏珠";至于凤凰,化成城东的"凤凰山",城西北的"凤凰台",护城兆祥。因此,又名"五灵城"。传说毕竟是传说,不足为凭,文物考古为证。地处中华腹地,依偎黄河母亲,有山有水,最适于人类繁衍生息;上有三门峡,下有八里胡同,是黄河从黄土高原流向中原大地的最后一座城廓。上世纪初,中外科学家就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从年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在寨坪的土桥沟找到中国第一块始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百余年来,在古城及其周边的考古发掘一直就没停歇过。商城遗址、东关遗址、宋代遗迹相继发现。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在这里都有。一座灰坑发掘出一种文化,一堆瓦砾拼起一个朝代。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瓷器、铜器。古城的历史都在这坛坛罐罐里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寨坪土桥沟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具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曙猿化石,更是惊俗骇世,天下哗然。把人类出现的历史向前推进了l万年。证实了人类远祖起源于此。在今天的新古城街头,赫然矗立起巨石,写着"人类从这里走来"。天下谁敢出此言?唯独山西垣曲古城。志书中这样记述的:"……北靠历山,南频黄河,东辅屋,西弼中条。封门口扼其左,横岭关制其右。沇河、亳清河分东西合抱,气候湿和,土地肥沃,即为晋豫孔道,又为富庶之地,便交通,利农耕……"。确为钟灵毓秀之地,"葛伯春耕"、"阳壶返照"、"洪庆晓钟"、"黛嵋晴岚",垣曲古八景这里就有一半。清河口逮鱼,墩底下摸蟹,南河捉鳖,沙燕窝掏鸟,南坡上逮蝎,东河滩养鱼,南门口种菜,黄河滩上果园、花生……。三十岁以上的古城人,谁无此等记忆。日军占领期间的垣曲古城东街城在台塬上,北高南低,呈坡状,象是挂在天地间的一幅画。是城当然有城墙,城墙依地势绕城构筑,象是镶了个框。条石筑基,夯土筑墙,青砖包面,高大浑厚。墙头可以行人走马。不知道有没有城垛,有没有角楼就不知了。岁月和历史只留下残垣断壁。城门有三座。北门叫"富春门",南门叫"万安门",西门是"永丰门"。没有东门。相传开了东门,要出"一石二斗芝麻官"。即然能出官,为啥不开?其实东门外就是东河槽,东河水急,难免惹事生非。没开东门,出不了一石二斗的芝麻官,倒是住了不少人家,叫"东关"。西门也没有了,残缺的城墙,不深的壕沟,分出城内城外。一大片的人家,叫"西关"。据说当年的阎家沟和大赵村就是这里。古城北门
城南是河滩。是全城最低的地方,城里的水都往这里流,也有城墙,墙根有流水的涵洞,叫"水门"。城墙外就是南河,发了水,河里的水要进去,城里的水要出来,厚实的城墙也奈何不得。县志里记载的"城南频遭水灾,城墙屡圮"就是这里。县城的搬迁,就是这地方惹的祸。南门也早已没有了踪影,有门就有关。出了南门就是河滩,"关"不能在河滩里,有失体面。但关还得有,过了河是寨坪的东端,坪头有人家,属城里管,就算是南关。地势高,能看得见黄河,过去有观河亭,有刻着"天上来"的石碑,叫"南观"。垣曲话"关"和"观"的发音很独特,上扬下平的语气一听就知道是"关"还是"观"。外地人辨声听音,又谁去咬文嚼字地问是"南关"还是"南观"呢?北门还在,只是成了土台子。门洞被垒往了,当年县太爷骑马坐轿的风风光光、百姓商贾进进出出的煕熙攘攘,都被垒进了门洞。城门上"富春门"的匾额被岁月剥蚀的依稀可辨。门楼顶上有稀稀疏疏的茅草,几株永远长不高的椿树、构树,向人们诉说昔日的春秋,曾经的繁荣。城墙、城门,就象住户宅院的院墙和大门。在中国历史上,城墙,城门,是城的标志,权力的象征,繁荣的体现。有了城墙、城门就有了关,成了城关。一个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被这围在这高大厚重的城墙中了。我们无法去追溯历朝历代县衙官府的行政机构,那是文物考古的事了。人们的记忆存储在近代史上。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直是县治所在。世事更迭,时局动荡,国民政府,伪顽政权,日本侵略,都以城为目标,进了城就是有了名份,占了城就是占了县。垣曲的大事要事都发生在城关,城关发生的事就是垣曲的事。据说,流传至今的垣曲"催眠曲":"昂、昂、逗价价"中的"麻胡"就是从城里"蹩"(蹿)到东滩的。解放后多少年,还有山里的老大娘问:"城里的日本人走了没有"。可见,当年的城关在县里人心中的地位。古城社火汇演
新中国成立后,五灵城凤凰涅槃,欲火重生。人民政权在这不大的城里设署办公。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排民房就是县委、政府,公、检、法在三间瓦屋里办公。"仓堎上"是文教系统,"水门底下"是农业单位。县委书记、县长借宿百姓家,四合院里住着农户,也住着县里的干部。当然,作为新的政权,也要建设,盖几间瓦房就成了好单位,房子建的大,盖的高就成了大礼堂。以至于若千年后,城里人还把当年的机关单位作为地标,如数家珍地说当年政府就在这里,那儿是公安局,那儿是文化馆。当然也有人津津乐道地说:县长就住在我院的东厦;组织部长和我是邻居;县委书记的小娃和我一块耍大。年,县城搬走了,机关单位搬走了。留下了城关,留下了城,也给城关人留下诸多遗憾——县城要在咱城关,一定建好了;县城要不走,咱就是城里人;县城要不搬,咱也不用坐车跑六七十里去县城;今天也不用去城里卖房,往县城里挤。城还是那座城,只是少了一个"县"字,性质就变了,内容也不一样了,后来加了一个"古"字,也只能说明历史上曾作为县城。叫"古县城"或"老县城"最恰如其分,当然太俗了,也有些绕口。是城当然有市。对县里人来说,最具诱惑,最让羡慕的当属城里的街市了。据说原先的街道是在后来的石坡上,你咋也想象不出曾经作为老城街道的存在。拐拐弯弯的曲里通幽。七尺竹竿横着都拿不过来。路面倒是用卵石铺成的,不扬尘,不沾泥,只是走在上面咯脚,幸好当年没有流行高跟鞋。至于商铺,没有留下丁点的迹象,到后来两边的院落大门连檐接拱勾心斗角地成了胡同。后来的街道不知是啥年代开的。北城门西边的城墙挖开了一个豁口,一边各垒了一个高高的砖柱,顶上有一个石灰捏成的圆球,用红颜色抹了色,没几年就成了灰不拉几。倒是用铁条打的弓形半圆,顶在两根柱顶上面,锈锈斑斑地存在了好多年。街道通到了南门口。街不长不宽,坡依然存在,走不远就下坡,两边的房屋顺坡构筑,呈阶梯形,一溜的南高北低。走在街上,朝南看,只见得一颗颗的头顶,向北看,是一条条的长腿。往南走,得抬头挺胸;朝北走,要俯首弯腰。山里的城,要符合山里的特点,上山下坡地惯了,平了,大概就走不成路了。街不长,不用极目,就瞅到了街头。北门口一声吆喝,南门口都能听到,一家炒辣椒,满街打喷嚏;一家饭铺熬羊汤,满街都是膻腥味。南北一条街,东西也有一条街,号称"十字街"。只是"十字"的这一横写的太短,东走百十来步就到了城壕沟,往西四、五十步就进了戏台院。过了十字街,是条丁字街。只有西边一截。历来是行政中心,原先县委、县政府机关单位都在这一片,后来镇政府、招待所、法庭、税务所、党校、农机公司都在这条街上。东济公路从西关进来,穿城而过,即是街又是路。到街口,司机刹车踩的不准,方向盘扭的不到位,还要打倒车才能拐过来。街口的房角常被刮蹭,汽车开进门市部的事时有发生。因为曾经是县城,因为历史太悠久了,因为县城搬走了,因为要修小浪底水库,大概也因为这地方迟早要淹没。几十年间,街道格局不变,建筑不变,瓦房与楼房并存,土墙与砖墙都有。就是门脸,有一块块木板拼装的栅板门,有安合页的新式门,也有时髦的玻璃门。走在街上,恍惚从民国到现代一路走来。如果没有搬迁,稍作美工,一定是不错的影视拍摄基地。就是这么长,就是这么宽,就是这么几道街。商品不以街道的长短而缺失,买卖不因门市的大小而兴衰。供销社、信用社,粮站、棉花站,农机站,食品站、副食加工厂、药材公司,新华书店,照相馆、镶牙馆,理发馆,裁缝铺,黑白铁,油坊、弹花柜、铁匠炉、药铺、饭铺、旅店,招待所,卫生院,兽医站在这不大的街道上都有一席之地。吃的、住的、穿的、用的,都有卖的,都能买到。大街上,卖菜的过来撂下担子就有了交易,搁张桌子就有人抜牙,放把小凳就开始割鸡眼,就连丁字街而南角也放一把用布包裹的大茶壶,是卖油茶的。长了,吊涎;短了,局促。宽了,空荡;窄了,拥挤。三五个人走在街上不显的寒碜,十个八个人在街上就有了热闹。只是每年四月初八,腊月初八的两次会,就有些拥挤不堪了。四面的货来了,八方的人来了。卖买多,人多。到处摆摊,满街是人。北来的从北门口挤到南门口,南来的从南门口挤到北门口,凡正就是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到处是人挤人。摆摊人叉开两条腿,展开两只胳膊护着摊子,那能顾得卖货。拿杈把扫帚的得朝天竖,钉把镰买把锨也要举起来,一不小心就蹭剐了别人的衣服,伤了皮肉。买顶草帽戴在头上,抬手一摸没有了,回过头看看,别人头上也是戴着草帽,岂敢槽头认马,头顶夺冠。有往前走的,一个劲地喊:"油"、"油"、"油",起初兴许还有人躲闪。吆喝多了也不灵了。赶一天会,出几身汗,踩坏了鞋,挤丟了钱,不说地方小,只说"会"热闹。倒也是,平日里山坡野岭地松散惯了,只有一年城关的这两次会,才能享受到如此的拥挤。何况赶的是城里的会,在城里挨的挤。再受症也感到愜意。古城的狮子表演从私营到国营,从商号到门市部,多少年来,城里的街道没变,生意也没变。山里的城,山里的人,人们对城关的商业记忆仍然是梅氏镰,张氏镢,老谢照相、老韩镶牙,李家的裁缝铺,赵家的绸缎行,百顺娘的油茶,丁酉的饹唠锅盔……如今说起当年老古城的街市,连说带比划,要不拾根草梗,在地上给你划拉一番。用地图为你演示方位地点,有形有色,甚至都让你觉得有了味道。虽然古城躺在了水底,但淹没不了人们对物产的怀念,乡愁的记忆。两千年的县治历史,积淀了厚重的文化。三大楼,四大祠,八大坊,二十五座寺观,八座祠堂,四大花园,六大门楼在这块土地上堆砌起厚重的文化底蕴。在《古城村志》中,有记载的寺院庙宇就有四十多座。兴国寺、关帝庙,汤王庙、泰山庙、龙王庙、土地庙,文庙、武庙、土地庙、财神庙、药王庙、玉皇庙,帝君庙、娘娘庙,四圣庙、马王庙、瘟神庙,圣母庙、衙庙,各路神仙都来城里凑热闹,楼、亭、阁、坛、塔、祠、堂、牌坊、祠堂不尽其数:赵家楼、三节楼、钟楼;观河亭、茶亭、迎春亭、景亳亭、申明亭;魁星阁、文昌阁、文成阁、文星阁;回澜塔、社稷坛、先农坛、祭公坛、邑坛、风云雷电山川坛;关帝庙牌坊,文魁牌坊,龙门牌坊,刘家牌坊、赵家牌坊,席家牌坊,李氏石牌坊;土地祠、崇德祠、节教祠,乡贤祠;席家、李家,张家,姚家、文家、鲁家,马家、赵家、刘家、申家、王家,各家都有祠堂。牌坊高耸,楼塔拔地,庙祠辉煌,亭阁轻盈。庙有神,阁有文,牌坊有对联,祠堂里有先祖牌位。为这座古城,凭添几分光彩,彰显文化厚重。只可惜,世事更迭,战火焚燃,天灾人祸,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只有兴国寺高高的坡道还在。赵家楼的废墟还在,其它的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口头中,记忆里。到后来,常有传言:城里某家盖房挖根基挖出了几罐银元,某人拆房时发现大梁上搁着一包金条,某家的墙缝里滚出了元宝。甚至那年说是发现了某家的地道,寻来金属探测器鼓捣了一番。这等传言,可信也不可信。不过,这块土地上的文物确实曾经存在,后来被写进古城村志中,留在了纸上。 是城,也是村,是垣曲最大的村。大概那个年代没有城建部门,当然没有统一规划,几千人口挤在这不大的城垣内外,有崖就掏窑,平地盖房厦。依地而居,各自为战。官府与民居共筑,胡同和巷道交织,住宅门户相对,房檐勾心斗角,横七竖八,错综复杂。北方的胡同,南方的里弄,城里都有。东关、西关、北门外,南门口、石坡上、水门底下、城壕沟、后地、仓堎、十字、赵家胡同、孙家圪台,陋巷、席家巷、鲁家巷,学道巷、敦厚巷、马道巷、仁和里,每个地名都有来历和说法,或地理,或方位,或典故,或传说。纯朴实在,轻巧文明都体现在这名字中了。只是纵纵横横的让人难找,有笑谈说:乡下姑娘嫁到城里,得一年半载认门。就连土生土长的城里人也分不清楚。以至到后来,就以生产队时期的区划作为居住地的地标,一队北城外、后窑、北城里;二队石坡上;三队东街;四队东关;五队南观上;六队水门底下;七队西门内、仁和里巷;八队西城外;九队后地;十队城东南角。村大人多,不可能都认识。说:"我家是古城的",往往得问一句:"几队的"?答:"四队的"。"噢,东关哩"。搬迁这些年了,古城人的乡愁在脑海中刻下永远的印迹。就象侯鸟一样,迁徙的路途再远,繁衍生息之地永远不会变。以至现在仍按老古城的地理环境确定方位,识人断物。在南河畅游的孩子
最值得称道的要数城里的住宅了,有窑洞,有房厦,有三合院,四合院,也有土木结构的房,钢筋水泥的楼。墙有土筑的,有胡基垒的,有砖土混合的,有钢筋水泥的。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各时代的建筑风格。通天门窗,十二扇栉,古香古色;影壁,照壁美伦美奂;木雕、砖雕玲珑剔透。匾额题写着"乐天倫","听三声","福祿寿"、"荷鹿同春",也有"耕读传家"、"风雷激"、"尽朝晖"。不起眼的门楼上赫然挂着"武魁"的匾牌,一座残缺的楼台上仍然卧着一对石狮……。古城特殊的地理条件,黄土高坡和中州平原在这里交汇,秦晋民风在这里沉淀,豫皖冀鲁的特色在这里体现。如果说"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是单体民宅的风貌,那么这里则是一座城中群体民居的集中展示。只可惜,移民搬迁,大部分被拆毁了,也有的流失了,不能不是遗憾。还好,在县博物馆的院子里,移建了几间民房,几座影壁,千百年古城民居文化淒淒凉凉地存在这一隅之地。多多少少留下一点念想。垣曲古城西街小学
城不是纯粹的城,村也不是一般的村。城外有地,种地打粮食;城内有街,街上做买卖。亦城亦村,亦农亦商,号称"卖买搅庄稼"。因而富户小康之家居多,有"四大家,八小家,七十二家平和家"的说法。出富户也出人材,在外干事的人多,翻开《古城村志》,人物占了很大篇幅,全国各地,台湾、港澳地区,就是国外都有古城人。在这里还应当提到,古城东边是豫西的济源,新乡;南边过了黄河是河南的渑池、新安,离洛阳不远,是黄河流向中州平原的最后一座县治城廓。历史上是商贸往来之地,也是中原逃难人西走的必经之地。作为县城,海纳百川,讲德守义,商贾往来,人材流动,吸收了新鲜事物,促进了经济繁荣。最早放映电影,最早有了电灯。最早有了裁缝铺,最先开了照相馆、镶牙馆、理发店,作为县城,在一定历史时期,城关是垣曲政治的风向标,经济的晴雨表,文化的发祥地。城里下场雨,乡下就涨河;城里挂条标语,乡下就是一场运动;城里有了酱油,乡下的锅里就有了颜色;城里时兴高跟鞋,乡下就有了"叭哒"声;城里兴起穿裙子,乡下姑娘"风摆柳";就连现在的垣曲名吃羊汤、饸饹、锅盔也是从古城的街上开始的。历史的积淀孕育出厚重的文化。民俗风情最具垣曲代表、言行举止最具垣曲形象。城里人说话白是pai,麦是麦,话出口来,侬言俚语地轻俏,柔软。不象乡下人白说成piai,麦说是miai;一句话一块石头,砸在地上一个坑,就是吵架用词也花样翻新,不象乡下人只会"你娘X"。城里人吃米粸、杂饭,也吃白粥、闷饭,只是吃饭用细瓷碗,待客碟是碟,盘是盘,饭做的汤是汤,菜是菜,有模有样。乡下唱蒲剧、曲剧,演古装戏;城里唱歌剧、话戏,演现代戏。乡下敲锣打鼓、城里打洋鼓吹洋号。当年的《古城新歌》唱响河东,《登攀》地区夺魁,就连地区文工团也邀请作示范演出。正月里闹红火,走旱船、推小车,跑竹马,打腰鼓,踩高跷,扭秧歌,样样数数多。南观耍狮,狮子能爬几丈高的绳索,在空中耍;申家舞龙,能喷火,会吐烟,摇头摆尾,腾云驾雾。看的乡下人直啧啧:城里人就是能,耍活都耍的不一样,会耍。每年元宵节县里组织游艺汇演,没有城里的耍活,就没看头啦。毕竟是县城,是垣曲的大城市。古城地势低,县里人看的高。说起城关,往往是:"城里"、"城价",语气中有羡慕也有嫉妒。进一趟城,如同今天出一次国。头几天就着手准备,浆洗衣服,做鞋,只怕左邻右舍不知道,进了城怕人笑话;走在路上,一身的光鲜,有人问:"走啥价"?"去城价——捎啥不?"小伙子能在城里说个媳妇,在村里腰板就硬了,头都扬起来了,美滋滋的。谁家姑娘在城里找个婆家,就连爹娘说话也气粗了。别人问:"婆家是哪里?"——"城里的"!话里掺和着笑声,甜滋滋的。东关小车城里和乡下本身就有差别,何况垣曲县就这一座城。一个时期,"俏"成了城关的代名词。"俏"在垣曲话中是个复合用字,含义很复杂,大约与实在、诚恳、厚道成反义,有精明,浮躁,虚渺的意思,也有羡慕、妒嫉的含义。比如:有人为图好看,大冷天穿的单薄,就说"看把你俏哩";有人说话俏皮,幽黙,也有人说这人说话"俏"。总之,字典中没有垣曲话中的"俏"字释义,很难做出垣曲话"俏"的确切的表述。这里借用这个字,与释义相差甚远,也委屈"俏"字了。前面提到城关人细致,吃饭用小碗,用细瓷碗,馍蒸的小,饭菜做的精致,乡下人就说是"俏";——其实这是饮食文明的体现。有段子说:来了客人,城里人嘴上留客吃饭,迟迟不搭锅,客人等不着,要走。送到门口,灶间"吱溜"一声响,"看看,菜都炒到锅里了,你非要走"——其实是烧红的火柱插进了泔水桶里。——作为城里人,客来人往的确实支应不起。后来又有现代版的:来了客人,问:"你吃了么"?客不好意思,答:"吃了"!又问:"你真吃啦"?"吃啦"!"不要撩"!一句接一句地问的客人更不好意思了,不语。——"吃了就算啦"——这是笑谈。.古城舞台其实,城关人也有过苦难。战火催残,攻村也是攻城。子弹飞溅,打老百姓也打当政者。城里人衣服上也有补钉,锅里也有清汤寡水。有过到乡下籴粮食,东坡上挖荆疙瘩,黛眉山拾柴,黄河边买柿瓣的经历。在那个年代,乡下日月不好过,城里人更艰难。乡下人好赖还能开小块地,点一窝南瓜,种几苗红薯。城里那有一片土去垦去种呢?就是捋洋槐花,捋榆钱,拾柿花,柿蒂,也得到城外,去乡下。"穷则思变"。城里人思变更心切。城里人也能吃得苦,耐得劳。几十年的光阴,几十年的奋斗,古城人用勤劳和智慧改变面貌:大战西河湾;南河滩修坝填地;东河滩修鱼池养鱼;凤凰台修建高灌站;寨坪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革开放后,古城人以精明和能干率先办起了电镀厂,玻璃厂,化工厂,手套厂,鞋厂,建筑队。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发挥城里人的聪明才智,种菜,栽果树,养鱼,搞种植养殖,办家庭副业,全县第一辆卡车是古城村买的,第一辆私营客车是古城人买的。古城的菜销到半个县,街上开商店,开饭店,办旅社,个体户林立,兴旺发达。真正的"卖买搅庄稼"。小浪底水库的修建,古城在淹没区,古城人舍不得这块土地,舍不得这片家园,权衡再三——后靠。新址选在凤凰台上,虽然没有"五灵"的风水,至少还有凤凰的庇护。规划、建设,历经寒暑,一波三折。年,小浪底水库蓄水,古城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故土,那段时间里,古城人站在库边,面对一片废墟,眼看着上涨的水位,指指点点。那里是我的家,那里我家的祖坟,水到南门口了,到十字街了,到石坡上了,到北门口了,水一截一截地升,心一点一点地紧,眼噙热泪,心在滴血,古城人用这种方式,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向生吾养吾的土地作最后的诀别。古城,这座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古城,终于沉在了水底,古城的历史,古城的辉煌永远存留在了水底,只留下了古城这个名字。古城眺望狮子山曾经的古城,曾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年的县城搬迁把政治搬走了,年的移民搬迁又把经济留在了库底。如果说县城的搬迁,曾经给古城人留下失落和遗憾,那么,这一次的搬迁,留给古城人的是无尽的惆怅和永远的怀念。如今,村搬到新地,名子也跟到新地,仍然叫古城。十里长街处处有古城,处处是古城。城南有八队,城北也是八队,原先以队识居地的话中,现在又加上了沇岭、磨头、堡头、店头这些村名的注释,成了复合村名,有借居别村之嫌。稍有欣慰的是,移民搬迁,辙乡并镇,古城镇建制没变。谭家乡划归古城镇,东河槽都成了古城,村名镇名都叫古城,有谁去刨根问底是村还是镇。村还是古城村,镇还是古城镇。迁居新地,民居整齐漂亮,街道平坦宽畅,十里长街,全都门朝街开,店铺格局,开门营业的少。虽然烟酒副食,百货日杂,五金交电都有,但是"十亩地里撒进一把黑豆",时常是空空荡荡,冷冷静静。就是全然没有老古城的韵味,没有老古城的热烈,也没有了老古城的繁荣。就是四月初八,腊月初八也海阔天空地热闹不起来。有饭铺,仍然卖饹饹、锅盔、羊汤,但不闻四溢的香味,更没有诱人的膻腥。没有了老古城的拥挤和热烈,也没有了老古城的韵味和繁荣。本来就人多地少。淹没,淹了房也淹了地;搬迁,地搬不出来。西河湾的米粮仓,南河滩的菜地,寨坪的富庶,凤凰台的丰绕,槐树凹的旱涝保收都留在了库底。有山有水,有坡有滩,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大口井,电灌站,河坝、旱能浇,涝能排,原先所拥有的诸多自然优势,以及依赖于这些优势而长期形成的一些高效农业更是不复存在。虽然也从附近村征了地,但"杯水车薪",每人几分地,而且十里八里地远。五灵城,龙去、牛走,只留得两只凤凰对湖而歌。护佑着新的古城。买卖少了,庄稼搅不成,古城人惆怅而无奈。眼瞅着东原辣椒红,西原核桃绿;昔日落后的英言发达了,邻近的王茅赶上来了,古城人心里咋不着急,咋不为昔日垣曲第一镇的失落败北而焦心,为城里人的称号而羞愧。好在古城的文化还在,人气还在,精明能干还在,勤劳智慧还在,血液中流淌着龙的血脉和精神,骨肉中存留着牛的坚韧和毅力。古城人不气馁,不失落,奋起直追。养鸡养猪,种大棚菜,科学种田,高效农业,让有限的土地上发挥最大的效益。小浪底宽阔的水域为古城转型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农民变渔民,农产转水产,捕鱼捞虾,网箱养鱼,开发水上运输。古城国家湿地的建设为古城带来新的机遇,发展湿地旅游,办农家乐,植树栽柳,学习柳编工艺,开发湿地产品。昨日已成历史,今日更须努力,百尺水下曾经是我故土,湿地侧畔创建新家园。我们是黄河儿女,我们是古城人,龙要腾飞,牛须奋蹄,凤凰涅槃。古城一定能崛起,一定能富强,一定能实现梦想,也一定能担当起古城的称谓。——载年4月7日、11日《运城日报》第三版你若喜欢,请在文末点赞,并点击“在看”[黄河原创文学]已经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运城网信备案L31号
黄河原创文学推广团队
特邀顾问:申大局 王士敏 张开生
本刊主编:姚普俊
图文编辑:谭瑞平
小说审编:谭锐金 郭 英
散文审编:李亚玲
诗歌审编:王秀娥
校园审编:靳三涛
投稿邮箱:
qq.转载请注明:http://www.gmzwc.com/jyzd/12385.html
- 上一篇文章: 如何通过唇色诊断辨证带有验案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